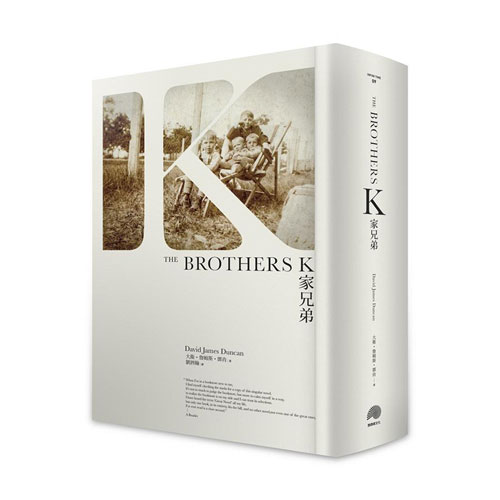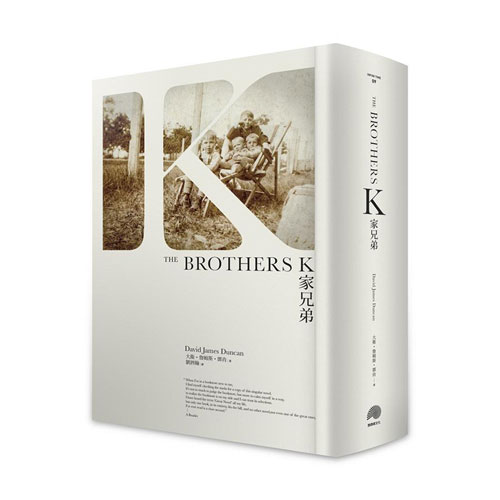好球帶
沒有什麼是靜止不動的,
所有一切都搖擺不定。
──約翰•吉拉赫(John Gierach)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老爹教我什麼是好球帶的那一天,,一個溫暖得不可思議的四月夜晚。我看到他身上穿著髒兮兮的工作服,手裡抱著刷子、一品脫的稀釋劑和四分之一罐白漆,步履維艱的從車庫走出來。
老爹從口袋裡掏出半截粉筆,走到靠在牆上的破床墊前面,開始畫了起來。其實他沒有畫什麼東西,只是用粉筆畫了一個大約十五吋寬、三吋高的長方形,甚至還沒特別費神把長方形的四個邊畫直;我這會兒知道他是要畫一個投球時可以瞄準的目標,而且打算在畫好之後漆成白色,可是我不知道的是:這個看似簡單的工作為什麼會讓他苦著臉煩惱那麼久呢?他拿起皮尺來測量剛剛用粉筆畫出來的長方形,然後低聲駡了一句粗話,隨手抓起一塊破布,狠狠的擦掉,接著又畫了另外一個長方形,比第一個稍微短了一點。可是過了幾秒鐘之後,他用力地把皮尺丟向那個長方形,又駡了一句粗話,再把這個也擦掉。接著,他轉頭看著我,突然說:「畫什麼好球帶,一點意義也沒有!」
我知道這時候不該開口說話,更不應該發脾氣,於是靜靜的從牆邊站直。
「為什麼?」老爹問道。「為什麼固定的好球帶沒有意義?」
我是真的不知道,所以就很誠實的聳聳肩。
「認真想一想!」他怒斥道。「假設我們畫了一個長方形的好球帶,適合六呎高的打擊者,但是卻遺漏了高一點或矮一點的打擊者,這是最明顯的一個缺點。但是還有一個更深的缺點,也是最重要的缺點:一個六呎高的打擊者,他的好球帶究竟在哪裡呢?每一個球員的好球帶又在哪裡?」
我照他說的,認真地想了一想,可是最後還是不得不聳肩。可是這一次老爹卻大喊一聲:「對!」然後開心的在我背上重重拍了一掌。
「沒有人能說好球帶究竟在哪裡的原因,」他熱切的說,「是因為真正的好球帶根本與本壘板的寬度或是打擊者的身材無關;真正的好球帶其實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是不是這樣?小凱?是不是呢?」
我知道才有鬼哩!我唯一知道的是他開始讓我想起某個人,但是在我還來不及想到是誰之前,他就已經在發表高見:「他媽的,沒錯!就是這樣!真正要緊的好球帶,我們真的必須去克服的唯一好球帶,就是那個鎖在主審裁判腦子裡的好球帶!所以啊,我的孩子!好球帶不是長方形,也沒有什麼清楚的界線,更不是什麼跟本壘板一樣寬、膝蓋以上腋窩以下的範圍!好球帶根本他媽的是個幻覺,就是這樣啊,小凱!那是一個虛構出來的東西!是一把幾何形狀的鬼火!棲息在主審裁判一板一眼的小腦袋瓜深處的枝椏上!」
「所以說,都是在腦子裡,」老爹說。
「腦子裡,」我覆誦一次。
「好球帶只存在腦子裡。」
「在腦子裡。」
「不要忘了!」
「不會。」
就這樣,老爹僵在那裡,倒也不是真的僵掉了,毋寧說他是站在費了好大功夫才用粉筆畫出來的界線前面,一動也不動,彷彿他會一整晚都留在那裡似的。突然間,他整個身子蜷起來,奮力將手上的粉筆拋到冷杉居公寓的屋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