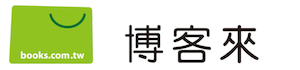少年時,讀范成大的《元夕後連陰》,裡面有一句:「誰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涼州百面雷。」覺得灼目,有千般好。大約是寒雨封鎖了樓臺,花失了信期,范大人久不見花開,便生出這擊鼓催花的念頭,文雅之中還泛著一股朗朗的英豪氣,讀來心裡都是痛快的。
那時我尚是十七八歲,驚鴻一樣的年紀恰似春風辭筆,將風光描摹得無限溫柔。總笑嘆,花信尚早,時間十分充足,即使大把大把地揮霍也不覺得奢侈。像是立春,多美好的節氣,是青色的暖,是明色的簪,是盎然的媚衣,是折花的裙裾。素年錦時,時光過得慢,心中也不著急,卻也憧憬著自己將來會在純白歲月的盡處,漾出怎樣的清水眉目,長成怎樣的溫良女子。
而今,生活在塵世,朝朝暮暮孑然又繁華。
養過幾盆綠植,放在狹小的書桌上與雜亂的書籍為伴。因為記得某個少年在雨後的驚蟄裡寫下的句子,他說:「以後要在自己的房子裡種上幾盆植物,怡紅快綠的。每日在忙碌之後歸家看到層層疊疊的茂盛躍入眼底,心中總會升起細細的歡喜,即使那小歡喜可以忽略不計。」那些植物,後來在時光中都不明症狀地相繼死去。
天氣好的時候,坐在陽臺上吹笛,陽光淡淡的,金沙細雨一般,覆在眉睫裡。嘗試給遠方的友人寫信,用古典的信箋,黃底豎格,印有極淺的蘭花痕,適合工筆小楷。少年時代的友情如水,又清又淺又遠又近,看起來是涼的,觸到了又覺得溫暖。又像春天有風的夜晚,繁花一樹一樹開遍,泛著清寒的涼與明醉的月光。花下的少年,在月下站成透明,風一吹,白衣勝雪,梨花滿地春衫薄。在那之後的很多年裡,我見過很多開花的樹,遇見許多不同的人,卻再沒有過那樣的美好。
$ 232 元
原價 290
-
$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