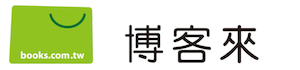在《共同體的邊界》一書中,普萊斯納對人類共同生活的諸種形式進行追問。在思考範式上,他繼承了滕尼斯關於“共同體”(Gemeinschaft)與“社會”(Gesellschaft)的著名區分,但他立足於哲學人類學視域,賦予這種理論圖式以不同的價值內涵:共同體秩序作為社會激進主義,對立於現代社會秩序。在他看來,只有社會才給人提供自我與他者、與自身之間必要的空間和距離,正是立足於這種空間和距離,人才能不斷地重新對自身進行構想和校驗。
《共同體的邊界》出版於1924年,時值魏瑪共和國的動盪歲月。普萊斯納的批判目標指向了當時的反魏瑪共和國的思想運動:無論是德國右翼青年運動所追求的“血緣共同體”,還是德國左翼運動所構想的“事業共同體”,都是在通過某種激進主義顛覆現代社會關係。在當時的德國知識界,這種理論聲音是孤單的。20世紀80年代,這部著作才被重新發現,引起國際理論界的廣泛興趣。
共同體的邊界:社會激進主義批判 (電子書)
- 作者: (德)赫爾穆特.普萊斯納
-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責任公司
- 出版日期: 2022-09-01
- ISBN碼: 9787208177178
- 編號: E050181343
$ 168 元
原價 210
-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