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一
讓我們祝福不被祝福 折磨還不夠被折磨……
打從一開始,閱讀柏煜,對我來說,就是近乎愉快的享受。
我們有過一段對話,隱喻地來說,是我問他,是否非常擅長發暗器,但沒練過刀。通常年輕作者在這時,都會為自己辯駁,沒想到柏煜老實到這個地步,直接承認,差不多就是這樣。這個問題在我心裡,頗有一番沉吟,我的想法是,就把暗器練到出神入化,練不練刀也無關緊要;因為人有天生性情稟賦,有人練十八般武藝,有人一招精純。後者的化境,有時也是可以在一招之中,蘊藏絕學。當然,就像對武功是什麼一樣,碰到文學是什麼,我們也有很多麻煩的刻板印象擋在路上,像柏煜這種不走大動作的路數,形象上,在最初的時候,難免吃虧。沒有相當的天真定慧,這條路走不長,而我碰巧是對這種可能性,強烈抱有期望,並且深深偏愛──所以,一向對任何人都不聞不問的我,也曾因為掛念,而藉著巧合,打聽他近況。我得到的多方消息,匯整起來,大概就是「超忙,忙著談戀愛」──除此之外無大事。這就對了──我聽了很高興。
戀愛最有志氣
我絕對不是唯一認為「戀愛最有志氣」的人。詩人里爾克慨歎過男子用情粗疏,應以女子情思繁複為尊;說到文學史某一時期的法國作家,個個沒有多少實際戀愛經驗,導致下筆空空不足觀──文學評論家莫洛亞的態度,則近乎羞慚;最「偏激」的小說家島崎藤村,甚至藉著小說人物之口說出:「就算有關係,如果不是男女關係,就不會真正想要解救對方。」(《新生》)──當時同志不若今日進入公共意識,以現下的話來說,就是,能讓人投入到捨己為人的關係,非戀愛莫屬。這是把戀愛看成唯一深化人我關係與存在使命感的信仰或倫理形式了。至於寫非正統推理小說的加納朋子,作品中也有過一番有意思的話,表示:戀愛是醜陋的事,不談戀愛的人排拒醜陋,所以也是不能信賴的人。(《七歲小孩》)
以上四家,重點略異,共通點則在於,意識到「情愛非小,文學當責」──讀者如果稍微了解這個來自各方的「唯戀主義」傳統以及多面性,會更容易進入《弄泡泡的人》的脈絡,總而言之,《弄泡泡的人》會使里爾克大大滿意男子已經迎頭趕上、莫洛亞不再搥心肝、島崎藤村慶幸吾道不孤──朋子則道:醜得很,可以信賴。
話說回來,戀愛與書寫戀愛,並不是同一回事。宅心仁厚的褚威格,在討論大情人卡薩諾瓦的回憶錄時,提點過該作品的某些價值,然而對於其人其書之風格無味,戀情描述可怕地浮面單調,褚威格的譴責可以說是輕輕放過。──戀愛是一個如流沙般,經常被寫壞的領域。當我們有幸看到作者,非僅沒有深陷,還能在其上舞姿從容,如電亦如火,哎,心裡那份感動,真有說不出的滋味。《弄泡泡的人》,就是屬於非但能在流沙之上騰空,還能在跳躍與旋轉中,與流沙對視與對話的奇蹟之作。
忠誠與花,花與亂
輯子裡持續出現的人物包括尼克與布朗,雙方的家人以及諸位有名無名的「第三者」──忠誠或是忠誠不能,伴隨著等距不一的三角(即使有四角或五角,多角基本上是以三角為原型擴充與變化,所以我一律泛稱三角)關係型態反覆出現。李永熾在談志賀直哉的《暗夜行路》時,提到過日本德川時代的文學,曾出現一種樣貌,在其中「所有出現的人物都是為了這個主角的成長」,我感覺頗可與我們手中的這部作品的形式加以參照──因此,尼克不但自由地想像各個人物,其他角色相對的非中心與不完整,基本上,也是由於他們在中心人物心理與內省活動上「協助者」(可以是友是敵或是敵友不明)的「任務取向」。我認為這與更加粗礪寫實進入性關係活動的作品仍有不同。與後者相較,前者更側重在「我是誰?」的問題上,然而「我是誰?」無法在對著自己肚臍眼說話的過程中,構築面貌。自己對另一人,以及另一人以外的他人,意謂著什麼樣的存在,沒有經過一連串建立與破壞的作用力事件,尼克 / 我無法拼出自己的意義上的名字。換言之,這既是非常個人,卻也社會化的歷程。
以〈糖果〉為例,尼克可說犯了多項一般戀人渴求「涇渭分明」的大忌,他不但不是照著一對一的情侶關係行事,諸如拿曖昧對象做的糖給被背叛的情人布朗吃,這都不只是他很「花」,同時他也還很「亂」──這不是通曉規則,駝鳥兼世故地將不同情人分而治之,以得最大情感利益的投機者行為。尼克做法的另種玩火性,在於有意或無心地混淆了身邊人固定的自我界線,當布朗也表示了逾越與不要邊界的慾望,說自己想要抱糖果的作者,無論布朗這是自發或學人,展現超越佔有或撤除嫉妒,尼克卻對他下了清楚的禁令。這裡感情與心理的微妙之處,都值得細思與探勘。
曾聽過有人對邱妙津作品的一大反彈,謂:自己可以多情,同時又要求情人專一,惡霸。這種切入點往往令我笑出來,然而這當然並不能拿來當作理由否定文學成績。多年前,夏宇即寫下「在不忠的情況下∕又仍然嫉妒這稱作∕不識好歹」──這般名句的價值並不在於完成了高竿的笑罵,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它清醒地寫出「碰到情事,義理就歪掉」的實況報導──《弄泡泡的人》中,這種「不識好歹」,可說變化多端且層出不窮──有趣的是,我們並不會立即感受到世俗性的評斷,相反地,總是在迷宮盡頭回首那一瞬,我們才意識到,已與作者走了一段「該被雷劈」的情罪路。〈生日〉、〈公仔〉、〈平安夜〉與〈丈量〉多篇,都可以說是這種外部眼光沒規沒矩的「浪子」或是「追愛之人」,披露各人內在視角驅動「歧路不可不行」、情潮洶洶的佳構。
儘管我認為布朗與尼克的不對等性,與創作型態的原始結構有關,布朗仍然被處理得相當深刻、立體且感人:單親媽媽兼喪父的小孩,這個背景的經濟弱勢較單親有時更加一等,因為若非喪父,除非遇上極不負責的案例,父方的扶養費仍能支援一定程度的經濟安全,布朗「養」著自己的錢,感情的夢想也是「被養」,實際的狀況卻是一身打工的疲憊──尼克與他的處境雖不到天差地遠,但也足已使他與布朗有種隔岸觀火的距離──甚至猜疑與隔閡。〈搬家〉以雙重結構透視了同志生命的經常性議題,文章定格在非常具代表性的「同志經典時間」──要不要搬出原生家庭與情人共組家庭?在某種慢速播放中,一邊是守密同志身份(或被迫噤聲)而在原生家庭中的準孤兒寂寞;一邊是並非毫不戀(父母)家,親與愛左右召喚,也左右為難的熬煮──這且要加上布朗與尼克兩人也仍然不完全同步的心緒。儘管這是我們熟悉的主題變奏,然而,把其中的疏離與眷顧、幻想與現實掌握得如此到位,使得「家不夠溫暖,兩人世界也可能孤立飄搖」的複雜心理與文化的多重清冷穿透紙背,著實難得。
絕緣以到絕處,絕處以逢生
在這些作品中,同性之愛已經不是「犯禁感」的中心,而是潛入同志內在生命的真實時,必不可免的人性深度——因此,我們終於有了極端同志中心(不知有漢,何論魏晉)的感性與複雜度,這是過去同志文學擔負與外部社會解釋與對話時,某種源於生存歷史而經常犧牲掉的成份,而如今,許多曾被中和、稀釋或邊緣化的「同位素」,因著柏煜特殊的文學才情與聰明的努力,重新得到了活潑的提煉與復甦。無視社會壓力、無視讀者評價、甚至也無視潛在所寫對象同志族群可能有的迎拒感受——這種絕緣性,本就是文學得以「火中取栗」的原點與最珍貴的創作心理素質。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文學就是一種絕處逢生的藝術,不走到絕處,就沒有文學——這是《弄泡泡的人》令我們讚歎之處。然而也就是在這個將文學還給同志的漂亮進行式中,同志文學也因此完成了,絕不遜於任何非同志文學經典的精神任務:祝福不被祝福、等待不曾等待、折磨還不夠被折磨。我可以預見歷來用以否定普魯斯特或卡夫卡的說詞,比如過份敏感纖細與主旨曖昧等,都會落在陳柏煜身上,不過,也是在同時,所有曾被細膩、幽微與不可測之詩情層層餵養過的心靈,也註定會在柏煜的這些作品中,得到久旱逢甘霖的欣喜若狂。——一如我們初遇普魯斯特與卡夫卡。
◎張亦絢
推薦序二
我美麗的糖果男孩
Ⅰ
收到《弄泡泡的人》排版的影印,翻開第一頁,必需承認,我是誤闖進了一座歧路花園,遍地魅麗,空氣中滿滿的嗆鼻卻鮮烈的青春費洛蒙。面對所有企圖引人暈眩的陷阱,我與作者一起警醒著。
像我這樣一個世故的讀者,並沒有為入口的廣場弄泡泡的魔法師所迷惑,眼光穿越,這花園的邊界還是盡頭,有一座古老牌坊,「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繼續前行,有一座宮門,上面橫書四個大字,「孽海情天」,一副對聯,「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請容忍我不合時宜的古典脾胃吧。)
不,該是癡男怨男才對,都什麼年代了,情愛就是兩個人(以上)的事,分什麼同性異性,又何必假借什麼同志修辭,男男情愛也就是如此這般,遇合摩擦生火花,長愛憎,再回頭望,電光石火,煩惱、苦痛並快樂著。
作者陳柏煜,千真萬確的美少年寫書人,果然是二十一世紀版的警幻仙子?
更必需承認,這是讀者的幸福,誤入《弄泡泡的人》的流光幻影中,它為我一人召喚了在壯美與激情的巔峰殉死的三島由紀夫,以及葉石濤在《變形虹》(1968年)序文中譽為「有可怕才華的年輕作家之一」的林懷民。
Ⅱ
也總是一再讓我想到鵝籠中的陽羨書生,一如俄羅斯娃娃,從嘴裡吐出私藏的愛人再吐出私藏的愛人再吐出私藏的……,《弄泡泡的人》,從台灣島的北端飆到南端,炎陽之氣一路持續灌頂,布朗、尼克、丹利、糖果男孩、阿鐵,一個銜一個上場,逐愛而居的男孩環墟?上下求索(征伐?)的愛的版圖?每一個男孩名字是同一枝條上的花苞。他們的身與卻心是這樣的燄光,像上午的太陽往正午的天頂走,島至南的墾丁天時地利好適宜助燃,將兩人一起的時光轟轟地炮烙。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標的與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永恆堅貞的真心人?(再次抱歉,請再容忍我發神經想到搞笑港片《東成西就》的梁家輝、張國榮。)一個家似的窩巢,懸在日常生活的高枝?男孩與男孩,到最後不得不把彼此豢養成兩頭自囚的刺蝟。
所以,雖然老套到令人煩厭,還是得問:愛到底是什麼?
陳柏煜回答不了,大概也無意作答,過程遠比結果有更多的含金量,只是這畢竟是索愛的人的宿命,當其時都只能讓它從指縫滲走。
唯一唯一的救贖,寫信寫字吧,在那孤獨的時空,找回所有流失的金沙,立地成佛,供讀者摩挲體悟,譬如:
「我的信與字在那時已經達到它們價值的高點。寫甚麼都是黃金,寫甚麼都奇蹟,都是使盲人復明的手。」
Ⅲ
艾德蒙.懷特(Edmund White)在他濃厚自傳意味的小說《一個男孩的故事》(A Boy’s Own Story)有一小段,主述少年夢想著愛人攀爬大樹潛入房間帶他遠走高飛,但「他遲遲不來,一直延宕,很快地我將期待轉化成鄉愁。」
凌性傑巧妙地將南海路轉寫為男孩路,是的,此路有多長?他將走多遠?一彈指或一瞬,在蛻變為男人之前。
三島在《春雪》裡寫清顯與本多兩男孩,「是屬於同根植物所開出的不同形狀的花和葉吧」。
這或是最好的解答,足以用來比喻布朗與尼克。最大也是至福的差距是,花葉綻放榮枯有時,然此中有一人寫作,留下血肉之驅嗤嗤擦著時間前行的每一分一釐的光影。
我們跟著陳柏煜一眨眼也不眨的看著與他肌膚貼著肌膚的男孩,茫然不知盡頭何處,時間渾沌,其實什麼都不能做,看著他在他手臂上流著口水睡著了。我們知道,唾液裡有蛋白質、酶,終將微微地發酸發臭。
Ⅵ
一條藍灰色的長圍巾,是愛人的或是戀慕之人的?戀物如戀其主人就在眼前,至於是否不告而竊為己有,請搜索全文判斷。物比諸人更恆久,保證不變心不出走,是對方、他的完美象徵,是我心的神龕。
一千六百年前的華山畿傳說,一士子戀慕偶遇的陌生女子,相思成疾,其母為士子求得女子的一件蔽膝(以今之圍裙想像吧),祕藏士子席下,遂痊癒了(女子費洛蒙的緣故?)其後某日,癡男「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
日文所謂物哀,陳柏煜寫那條針織的長圍巾,簡直一則驚悚文,愛不如戀,戀不如慕,慕不如怨,得到即失去、擁有即毀壞的開始。
我討厭如此說但還是要說,這是我近來讀過最悲傷的哀豔文。
Ⅴ
讀「搬家」、「福安宮」、輯六「寫信給布朗」時,我借用余華的書名《十八歲出門遠行》為主旋律,更分心去苦勞網重讀「想像不家庭」專題,卻苦於不知如何應對,想想唯有敬重素讀吧。
對於有著漁獵、遊牧基因的男性,家,這封閉空間總是負擔。如何閃躲、迴避、逃離,是陳伯煜的糖果男孩們的執念,甚至是困獸之鬥。而單細胞似的獨生子女的九○後世代,親屬單位逐一泯滅,家或者是家的替代與演練,必然又是逃避不了的個人選擇。
我確實疑懼男孩們蝸牛殼似的房間,容不下那刁鑽的愛情巨靈,反之,也容不下男孩們狂野多變的心。
好吧,讓我假裝自己是布朗是尼克,我問自己,將來你會實踐天職成為父親嗎?你會做一個怎樣的父親?在你眼中,曾經那失語、臃腫且無有光彩的潰敗父親,你真正理解嗎?多年後,你將發覺,每一糖果男孩的心裡埋著自己父親的種子。畢竟,電影《以你的名字呼喚我》那溫柔理解的父親只能是一個夢幻。
Ⅵ
布朗當完兵後,搬回家住,在客廳餵魚缸裡的孔雀魚。彷彿前世今生,疊影般我又看到朱天文《荒人手記》的荒人逐日盯著缸裡的大肚魚,荒人好比雲端上的上帝,與魚一起天荒地老的寂寞著。
時間的饋贈。整整五十年前,林懷民在中篇小說〈安德烈.紀德的冬天〉寫盡他那世代的同性戀者的鬱悶、壓抑、無出路,「一種被放逐的、見不得日光的愛,一種沒有疤痕的傷,一種沒有解藥的蠱。發著冷青的光芒,每逢心靈的冬天、雨季,便隱隱作痛,燃遍全身,如風濕,唯有秦那雙蛇般的手才拂得平。」時間驅趕我們加速前進,那些禁忌、污名、罪惡的陳年積鬱得以一路拋棄了(唯勇敢做自己的同時,勇敢面對吧,歧視是人性)。這是生對了時代的糖果男孩們的幸福。
是以《弄泡泡的人》才是陳柏煜的第一本書,他已從容優雅地確立風格,寫出一座他專有的精緻繁複的迷宮花園,捧讀時,浮現的又是故宮文物那件珍品,直徑裡共有廿一層次的鏤雕象牙雲龍紋套球。
◎林俊頴



 天天爆殺
天天爆殺  今日66折
今日66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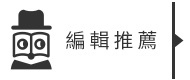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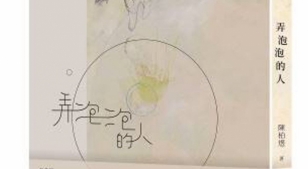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
博客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