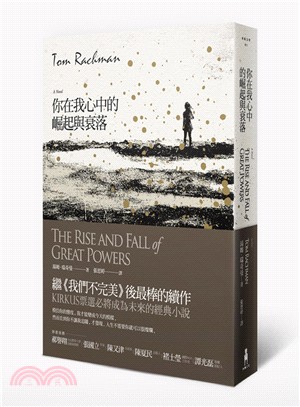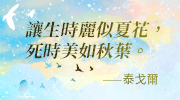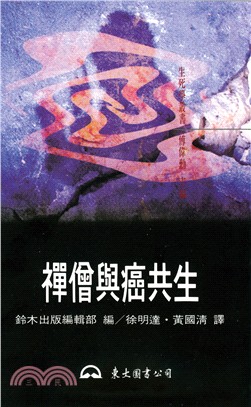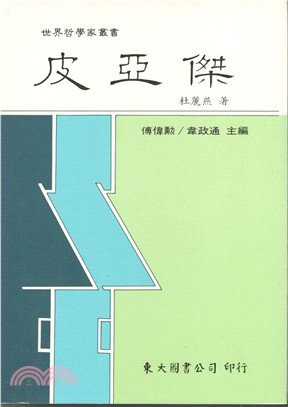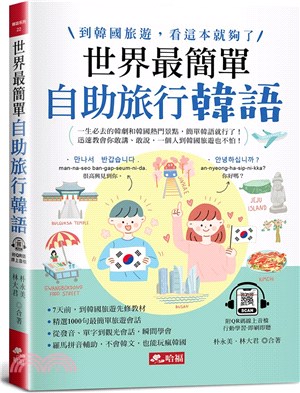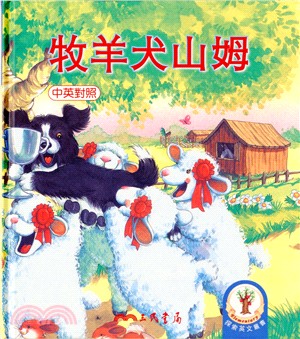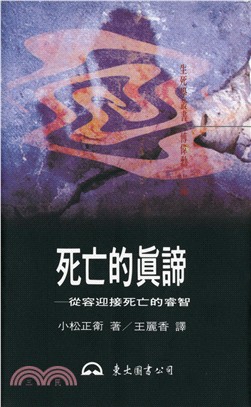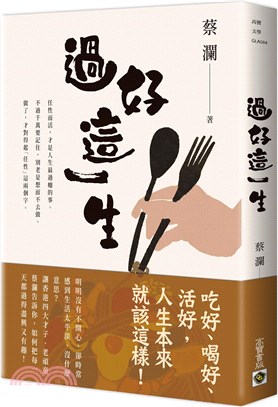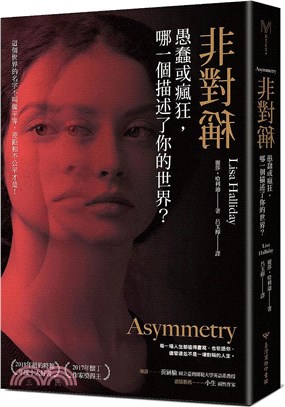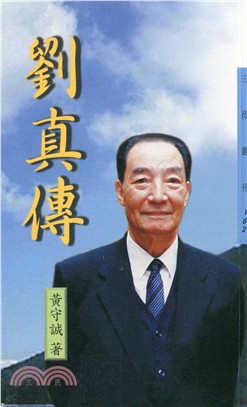商品簡介
也許有一天,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
就是我。
繼《我們不完美》後最棒的續作
Kirkus票選必將成為未來的經典小說
台北教育大學語創系教授 郝譽翔、作家 張國立、
小說家 陳又津、出版人 陳夏民、國際NGO工作者 褚士瑩、版權經紀人 譚光磊
――捧書推薦
這本書,獻給書店愛好者,獻給喜愛優美散文的人,獻給週末就想馬上讀完這本書的人。
――《新共和雜誌》
在威爾斯經營「世界盡頭」二手書店的杜麗很少談自己的事情,因為說出來可能沒幾個人會相信。在她很小的時候,杜麗就跟著父親到世界各地工作,直到某一天在曼谷,她遇見了自稱是她母親的女人。母親照顧得膩了,又把她丟給一個俄羅斯男人,杜麗喊他杭爹;那段日子,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是父女。
長大的杜麗喜歡闖進門沒鎖的公寓、捏造一個身分與過去,認識新朋友;而那個最照顧她的男人范恩——也是媽媽的男友——給了她一張信用卡,杜麗用裡頭的錢走遍世界各地,卻再也沒有這男人的消息。然後她頂下了「世界盡頭」二手書店。
直到有一天,前男友透過臉書,傳來她父親杭爹病重的消息——杜麗被迫從世界盡頭飛回紐約,飛回自己謎一般的過往。不稱職的親生母親與父親、她的代理父親、前男友、她真正在意的男人……這些曾在她心中崛起又衰落的人,該是給她一個答案的時候了。
模仿他的人生態度,杜麗才成為今天的模樣。
然而直到她無法再追隨,才發現,
人生不需要他就可以很燦爛。
作者簡介
湯姆.瑞奇曼 Tom Rachman
前美聯社駐羅馬特派員,《國際先鋒論壇報》巴黎辦公室編輯。目前為專職的文字創作者。他於1974年出生於倫敦,在加拿大溫哥華長大。大學時在多倫多大學念電影,後來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新聞碩士學位。自1998年起在紐約的美聯社負責海外新聞編輯,期間曾經到印度、斯里蘭卡、日本、南韓、土耳其和埃及等地採訪。2006年起開始提筆寫小說
譯者
張思婷
台大外文系學士,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生,世新大學英語系講師。熱愛翻譯。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
瑞奇曼這本千變萬化的小說告訴我們,所謂的家人有時是由你遇見和遇見你的人所組成。
――《書單雜誌》
這本書,獻給書店愛好者,獻給喜愛優美散文的人,獻給週末就想馬上讀完這本書的人。
――《新共和雜誌》
繼《我們不完美》後最棒的續作……這本書沒有屍體,但有引人入勝的身世之謎;雖然不需要知道「兇手的真實身分?」,但會想知道「主角的真實身分?」
――《西雅圖時報》
如果你正在書市中尋找一本筆法熟練、令人滿意的小說――就是那種從第一頁就吸引住目光,結局時才輕輕將你放下,讓你感到精神振奮、獲益良多――那你可以不要再看這段文字了,直接晃到你最喜歡的書店,買一本湯姆•瑞奇曼的新書《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
――《環球郵報》
即便故事背景橫越三塊大陸、時間超過三十年,湯姆•瑞奇曼的《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卻小巧精緻得令人感到驚訝――也許就是因為這樣才會如此好看。
――《影音俱樂部》
作者有精準的觀察力、錯綜複雜的故事結構,最後看似破碎的章節在瞬間合而為一。我想你一定會跟我一樣感到敬佩不已。
――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有的小說是最佳良伴,你實在很不希望故事結束。
――《每日電訊報》
這本小說訴說的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故事……但要表達的都是因為人類存在本身所產生的基本叩問:我們是誰?為何存在?但瑞奇曼的小說並不提供這些答案――說真的,怎麼可能提供呢?――它給我們的是一個極有價值的領悟,深入了我們對自我覺醒永不滿足的需求,還有一種極為深刻的欲望,以及無法逃避的那個問題:到底身而為人是何意義?
――《芝加哥論壇報》
湯姆•瑞奇曼第二部作品是一幅絕妙的拼圖。跨越四分之一世紀,碎片散落全世界……當這本書走到結尾,那股將一群角色拉緊的奇妙引力開始能看出端倪,並以令人滿足、甚至感到深刻的方式,顛覆主角和讀者原有的期待
――《英國衛報》
妙趣橫生,角色躍然紙上,故事的中心謎團直到最後一頁都緊緊揪住讀者的心。
――《赫芬頓郵報》
一個難以忘懷的故事。述說一名年輕女子重新回顧她充滿動亂的過去……結構精妙,文筆華麗。
――《科克斯書評》
這本小說帶著讀者跑遍世界、充滿緊張感……這趟旅程非常值得。
――《出版人週刊》
訴說著角色自身的謎團,講述書籍的力量,以及真相和小說有時無可避免,會交織在一起……本書令人難以抗拒。
――《圖書館週報》
人生的時時刻刻
小說家/陳又津
《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這麼硬的書,完了我怎麼可能看得下去。
湯姆‧瑞克曼說取這個書名有三個原因,其中一個是――節奏感!瀏覽十九世紀的經典書名《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娜》,(好萊塢電影也常常這麼做,比方說Leon),二十世紀演變至《人鼠之間》、《戰地鐘聲》,二十一世紀則像奇妙的詩句,瑞克曼瞎掰個例子,我想大概是《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我的妹妹哪有這麼可愛》的意思。想想我的品味……莫非還停留在十九世紀?(逃)
小說一開場沒多久,引述洛克語錄:
在我看來,書籍簡直像瘟疫靠這行吃飯的都要害病……害之以殘暴乖戾,舉凡印刷工、裝訂工、書商等只要跟書扯上關係並從中牟利的,大多性情古怪、思想腐敗,只曉得貪圖私利,不知替社會造福,破壞團結眾人的公平正義。
沒錯,我深以為然。世界要和平,社會要安定,焚書坑儒就對了啦。那種覺得自己是為了有趣而生的傢伙,工作好好的卻跑去寫書賣書,絕對是拉低全民GDP的兇手沒錯。
故事一開始在威爾斯鄉間書店,時間是公元二○一一年,顧客當然很少,少到老闆杜麗和店員可以聊天。不過杜麗以前的日子不是這樣,她的童年被流浪漢和妓女帶大,跟最像是她父親的男人旅行到曼谷。少女時期在紐約流浪,以「布魯克林分離主義共和國」為中心,徒步到附近區域,走進別人家說「我小時候住這裡有好多回憶可以看一眼嗎」,其實她只是想看看別人的生活,誰規定人一定要站在門外?沒人會懷疑一個年輕女孩,至少單純的大學生不會,於是這個身分不明的詐欺犯住進人家的出租公寓。杜麗三十歲出頭,那個《微物之神》所言「不老,也不年輕,一個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年紀,聽了俄國老書癡杭弗瑞的話,完成他所希望的「妳一定要搭火車到有趣的地方看一看,去做妳一直想做的事」。結果,她選擇在威爾斯一間破產的書店落腳。
小時候杜麗在流浪的路上遇到杭弗瑞,一老一小成了忘年之交,對話都脫不了書,萊布尼茲、休謨似乎隨時都在他們身邊。這些罪惡淵藪的書。從二十世紀苟延殘喘到二十一世紀的不合時宜者。杭弗瑞說:「我喜歡的人都在書上。」「我不是真的活著,我已經跟我的朋友一起作古了。留在二十世紀。」
但也許問題不在世紀之交,而是過去與現在的縫隙。瑞克曼剪碎了這個故事的時間軸,重新檢索過去的記憶,杜麗的經歷成了錯落的片段,三段時空以高難度的方式編織(是寫作技巧,閱讀倒是很流暢),平行世界光是有兩個就讓人頭大,但瑞克曼像糖果屋的哥哥撒下麵包屑,讓後來的讀者保持興趣,整體結構又不顯得呆。答案其實一開始就出現了,只是以為那是個疑問。所有問題兜攏之後,便能清楚看見瑞克曼的主題──杜麗擁有的不只是這個小說版本的人生,同樣的記憶與經驗,必須知道的資訊、必須拖延的疑問,經過不同的編織方式可能成為另外一本書。瑞克曼擅長描繪蕭條時代人類的各種變奏,第一本小說談報社,第二本是書籍出版,而這些如作者自言只是一種背景,他念茲在茲的是各種心靈。然而能解放這些心靈、撫平傷痕的永遠不是時間,不僅是時間,而是某種機關,一種運轉系統,重新檢索人生的時時刻刻,最接近這種狀態的,或許就是小說。
人們保留書不是為了再讀一遍,而是因為書中保留了過去……人也許被幽禁在自己的頭腦裡,整個人生都在想辦法從那上鎖的房間逃離。
在《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這本書,含金量高的句子到處都是,讓人會心一笑的段落也不在少數,讀著讀著,我們或許也能拾起自己部分的人生。
旅行者的風險
國際NGO工作者/褚士瑩
最近我有幾個喜歡旅行,足跡踏遍世界的朋友,不約而同在他們的臉書上分享了這段網路上出處不明的勵志小語:
試著跟你不同年齡層的人成為朋友。跟與你說的母語不同語言的人廝混。去認識一些跟你的社經地位背景不同的人。這就是你認識世界的祕訣。這就是讓你成長的方法。
("Become friends with people who aren’t your age. Hang out with people whose first language isn’t the same as yours. Get to know someone who doesn’t come from your social class. This is how you see the world. This is how you grow.")
作為一個旅行者,我實在太同意這段話裡的每一個字了。
比如說,你曾經試著將成熟的酪梨切開,突發奇想像奶油一樣抹在剛烤出來的熱吐司上嗎?如果沒有的話,有沒有想過,為什麼這樣的想法從來沒有出現過在腦海中?
日本的美食評論家來栖桂,到台灣後想到可以用在地的兩種簡單食材,製作了一款讓人驚豔的綠豆與台灣產茉莉花茶的果醬,從小到大生長在台灣的人,幾乎沒有人沒吃過綠豆湯,每個人也都喝過茉莉花茶,但卻從來沒有想過綠豆用糖熬煮後,以茶葉中單寧的苦味調和,可以成為一種全新的抹醬。
把幾種稀鬆平常的東西,放在一起以後變成一種不可思議的新東西,這樣的能力不是只有廚師有,也不是只表現在食物上,而是每一個有經驗的旅行者都會具備的能力,表現在生活各個細節中。
旅行的人,跟不旅行的人,逐漸地變成了地球村完全不同的兩種部落。兩個喜歡旅行的人,一個來自馬達加斯加,另一個來自台灣的花蓮,在葉門的旅途中遇到,兩人說完全不同的語言,但是他們一定會很快發現彼此之間的共通點,可能比起他們自己家鄉那些同文同種,卻從來沒有出過國門的人,更像同一族人。
湯姆•瑞奇曼在《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這本小說中,主角杜麗就是這樣,年紀輕輕跟隨著父親從澳洲到曼谷,最好的朋友是與父親同輩的莎拉,以及說起英語像母語的俄國人杭弗瑞,後來到威爾斯和英國的邊界頂下了一間二手書店,這些在不喜歡旅行、安土重遷的人眼中看起來,像是漂泊的不幸人生片段,卻是每一個喜歡旅行的人心目中的美好生命縮影。
書中的各種角色,輕鬆地切換在紐約,里斯本,巴賽隆納,雅加達、阿姆斯特丹、馬爾他、賽普勒斯、雅典、伊斯坦堡、米蘭、布達佩斯、布拉格、漢堡、馬賽,職業也隨著環境改變,從建築工人、超市肉販到酒吧經理,當鋪老闆的司機、老學究的知心、獨立的承包商、甚至有羅馬尼亞非法移民專門製造掛伊比利火腿用的鉤子。書中用「綁架」,隱喻在不旅行的人心目當中,各種旅行者所會面對的風險,代表各種最糟的狀況,但是書中的女主角杜麗,卻用極其輕鬆的方式描述綁架這件事:
「我綁架你沒關係嗎?」她問麥可。
「沒關係。」
「我們可以到處玩,去看五花八門的新奇事物。既不用上鋼琴課,也不用吃思樂康。」
他低下頭,對吃藥一事感到羞愧。 「我喜歡上鋼琴課。」
「這樣的話,我們只好找個鋼琴老師一起綁架。」
因為,旅行者對於生命的風險,有著另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
對於旅行者來說,不斷的移動本身並不算旅行,但永遠不停止「玩」的生命本身,當然就是一場旅行。無論遭遇到什麼別人眼中的好事、壞事,都沒有關係。
旅行者不是沒有危機意識的傻子,而是旅行者對於生命的風險這件事,看得比不旅行的人清楚。
旅行者的風險,無非就是把綠豆跟茉莉花茶一起煮成果醬的驚世駭俗,還有把酪梨抹在烤吐司上的離經叛道。
序
作者序 書名的玄機
作者/湯姆•瑞奇曼
為小說起名真是煞費苦心、絞盡腦汁、精深微妙。但書名真的這麼重要嗎?
對作者而言當然很重要。跟鍵盤纏鬥了好幾年,苦心經營十萬字,最後必須將這一切濃縮成短短一句,放在書背上。總要能點出全書旨趣吧?或許還要能朗朗上口。而且必須意味深遠、實話實說、莊嚴慎重、饒富興味、還要……
創作最新作品《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期間(稍後會解釋這書名的由來),我在便條本裡寫滿鋪陳故事的筆記。包括人物背景、時間軸、劇情線――此外還留了一頁發想書名。這頁在起草時是完全空白。到第一次改稿時,我寫了十來個。第二次改稿時,書名開始打架。不但每一行都是書名,有些還踡在邊邊角角。這些書名你推我擠,從紙上跳出來戳我的胸骨。有幾個還可以――但總是不太對。有幾個很完美――但不適合本書。而不堪用的還是佔了大多數。
接著,我靈機一動。有了。
我把靈感寫下來,在兩邊掛上書名號,彷彿想讓它胖一點,方便我細察。我前一本著作《我們不完美》的書名跟這本效果相仿,一來和內容互相呼應,二來突出原先輕描淡寫的細部。這兩個書名成為我後來改稿的依據:有哪些暗伏的細節值得多加琢磨,又有哪些細節活該遭到刪除。
有些書是從書名開始發展的,但我猜這種例子並不多。這種做法的風險是寫不出小說,反而是在起草概念。所以最好還是先讓文思泉湧,然後再拾掇、梳理、馴服。冠上書名的時機,我認為是在故事了然於胸之後。
不過,書名的選擇也跟當下的風潮有關。瞥一眼十九世紀的經典,便知當時偏好以主角為名,例如《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孤雛淚》(Oliver Twist)、《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二十世紀的作家則好用詩句,例如史坦貝克的《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典出蘇格蘭詩人彭斯(Robbie Burns),伊夫林沃的《一抔土》(A Handful of Dust)出自美國詩人艾略特(T. S. Eliot),海明威的《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引用英國詩人鄧約翰(John Donne)。如今流行的則是稀奇古怪兼詩情畫意,例如(我自己造的)《畢林索歌謠集的奇異溫柔》。這些破書名矯揉造作,又言不及義,頂多只能引人好奇。
回到拙作。這本書是小書店老闆杜麗・哲培博的故事。她在威爾斯鄉間經營一家滿是灰塵的書店,坐擁上百萬頁的書,顧客卻寥寥可數。她的身世離奇,在世界各地度過童年,被三個大人從一個國家帶到另一個國家,這三個大人湊在一起也很不尋常。他們養育她、教導她――然後人間蒸發。從此之後,杜麗對自己的來歷感到迷惑。有一天,某個舊識丟來訊息,促使愛好故事的杜麗拼湊出屬於自己的人生故事。
好了,來談書名吧。
《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有三層意涵。一是人生的興衰際遇:在孩提時累積權力,成年後把玩權力,年老後權力衰退――這三階段,本書幾位主角各自都經歷過。意義二,是世事的興盛衰微:本來你覺得不起眼的親戚,後來卻對他刮目相看,原本著迷的思想,後來卻覺得荒謬可笑。最後,所謂「Great Powers」還帶有傳統意義――也就是影響世局的帝國或政權,書中角色目睹了強權的興亡,思索自己在時代洪流中扮演的角色。
在《我們不完美》裡,我以數位時代和印刷時代的衝突為背景,細膩刻畫十一位角色的故事。在《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中,我將工筆描繪的故事搬到世界邊緣,以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為背景:從冷戰結束的一九八○年代開始,直到美國國力鼎盛的千禧年之交,再到科技和社會劇變的今日。劇情在這三段時空來回跳躍,將昔日的我們和今日的我們並置對比。
我的編輯非常謹慎地問我:這麼非小說的書名會不會有混淆讀者之虞?而且(編輯指出)還跟一九八七年保羅•甘迺迪的暢銷歷史書同名!那本討論世界政局的著作出版都要二十七年了,網路搜尋量會不會蓋過我的小說?這書名(不論跟我多有共鳴)真的值得冒這個險嗎?
就連受人敬重的喬治歐威爾都將《歐洲的最後一個人》改為《一九八四》,以迎合編輯的喜好。《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差一點就要叫《西卵的特里馬爾喬》。《第二十二條軍規》(Catch-22)原名《第十一條軍規》,為了銷售考量才將書名乘以二。
「名字又有什麼要緊?」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茱麗葉》裡如是問。「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故。」
《梅岡城故事》(To Kill a Mockingbird)就算叫做《亞惕》(哈波李考慮過要用這個書名),不還是一樣精彩?人和物給兜上了名字,大家就以為理所當然該這麼叫,就好比母親的名字雖然看似代表母親,但就算換了個名字(譬如希妲、艾波、梅麗),母親還是母親。
不是這樣的吧!你媽永遠不會叫希妲、艾波、梅麗――你媽的名字就是你媽的名字!書名也不能說換就換。
然而,聽完編輯的擔憂,我還是回頭把便條本裡的書名逐一考慮一遍,甚至把其他書名放上封面,看看效果如何。
但感覺都不對。我希望大家讀這本小說時,能有人思索一下書名,或許跟朋友討論一下,從中讀出另一層意涵——因為這本書叫《你在我心中的崛起與衰落》,而不是其他。
因此,我堅持己見。這本書似乎就該叫這個名字——如今就呈在你眼前。
書摘/試閱
2011:開始
數百年前,嵐托尼修道院的修士紛紛出走,諾曼哥德風的修道院日漸傾頹,屋頂塌陷後,留下石牆和石雕裸露在幾世紀的霪雨霏霏中,上頭爬滿芥色青苔,任憑風雨打穿曾經是聖壇的所在。
修道院遺址後頭矗立著黑山,這天早晨濃霧繚繞,她彷彿走進雲海裡,穿過薊草扎人的草原,經過吃草的羊群,直接攻上山腰。她越爬越高,濃霧漸漸散去,綠色的雨鞋走在滑溜的路上嘎吱嘎吱響,一步一步估量著腳下石頭的大小,兩條大腿痠得暢快。累歸累,腳步卻越來越急。
山頂的野風對她又推又拉,吹得她腰際的粗鉤針織衫不住翻飛。高原在眼前展開,望不到盡頭,石楠叢和歐洲蕨夾著白堊小徑,綿延數公里。這條山脊分隔兩塊國土,右邊是英格蘭,拼布似的大地以樹籬作縫線,拼起一塊塊圍著柵欄的農牧地。左邊是威爾斯,一叢叢漫生的濃綠,一幢幢石造的農舍,還有一片片險惡的樹林。
光影在土地上斑駁變化。她在陽光下止步,閉上眼吸收太陽的溫度。一連幾天不見陽光,太陽一露臉,她便提步去追逐。但最讓她興奮的還是雨。從書店的窗戶往外看,世界頓時安靜下來,路上半個行人也沒有。她對小雨沒興趣,要大雨滂沱才有意思――急雨在葉子上爆裂,咽住排水管,擂得書店的閣樓屋頂簡直像跟打鼓比響。一天午後,天空一陣響雷,弗格倒抽一口涼氣,把手頭那本講蒙古遊牧民族的書翻得沙沙作響,想借此掩蓋過去。
「暴雨很美,」她說。
「溼答答的。」
「膽子小就說嘛。大自然像這樣翻臉發威起來,不覺得很令人興奮嗎?」
「妳覺得地震很令人興奮嗎?」
「呃,如果只是在旁邊看――想像一下嘛――沒有人受傷,沒有造成任何損失,那麼,是的,地震真的是不可思議。就像照片上的岩漿一樣。」
「如果岩漿濺到妳身上,可就不好玩了吧。」
「岩漿從來沒有濺到我身上過啊。」
「我也沒有啊。雖然很殘酷,不過是實話。」
在緊閉的眼皮底下,她察覺到天色暗了下來。陽光在這片荒野上遷徙。一顆雨珠落到她的臉頰。細雨嘈嘈下了起來,野風吹斜了雨絲,一會兒轉向這邊,一會兒轉向那邊,好像海裡倉皇的魚群。她看著雨點一滴一滴打溼襯衫,棉料緊貼著她微隆的胸脯和纖細的腰身。二十歲時,她認為自己的身體跟她本人毫無關係,她只是住在一個跟內容分離的容器中。近來,她瞥見自己日漸消瘦的身軀,心裡想到的不是身形,而是光陰。歲月來了,她的粗糙是歲月侵蝕的痕跡。她看著雨鞋踐踏野草,睫毛上低垂的雨珠模糊了視線,隨著步伐不住顫抖。
一隻烏鴉從頭上飛過。嗯,這隻烏鴉很該穿件風衣。天上的鳥兒怕淋雨嗎?這問保羅就曉得了。不,只准想此時此地的事。兩條腿還在走,她深吸一口氣。什麼都別想,只管現下的感受,多快樂啊。如果要她寫一本書(她從來沒這個打算),大概會寫什麼都不想的快樂。我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愚蠢了?天曉得這樣會寫出什麼樣的書來。或許可以治好失眠吧,至少。
白堊小徑穿入樹林轉下山,經過農牧地,越過梯磴,穿過修道院遺址。上了飛雅特後,溼透的粗鉤針織衫被扔到後座,調一調後照鏡,她饒富興味地瞥了瞥淋成落湯雞的自己。回程是二十分鐘的單線道。她蜷起腳趾(每次大貨車從轉角衝出來她都會這樣),彎進樹籬裡,讓大貨車通過。她這輛車沒有避震器、沒有安全帶,震得人骨頭簡直要散架。乘客座沒窗戶,只用一塊塑膠布擋著,車子一開,塑膠布就啪噠啪噠拍打起來,從生鏽的車底小洞往下看,還可以看見路面的柏油。
杜麗把車停進教堂的停車場,麻雀(正爭奪著週末婚禮散落的米粒)振翅飛走。她在這個村莊住了快兩年,半個朋友也沒有。這地方人情澆薄,正合她的意。報攤、醫生、律師、警察。肉販學徒穿著紅白相間的條紋圍裙,一面抽菸一面騎腳踏車送貨。獨角獸街上賣派餅和薯條的店家。村子裡的鐘。紀念碑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犧牲的凱諾鎮子民」,以及底下的塑膠罌粟花圈。
當地人都喊她書店老闆娘,看她徒步在小徑上,頗有那麼一點異國情調――因為她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當地人都這麼說。她辯稱自己不是英國人。威爾斯人對「英國」很感冒,說起這兩個字的口吻很是簡慢。這位鄰居在禮拜天闖進人家的客廳,吃完人家的蛋糕,占盡所有的鋒頭。更糟的是,英語取代了威爾斯語,交通標誌上雖然還見的到這奇妙的語言(cerddwyr edrychwch i’r chwith,意思是行人注意左邊),但當地人大多連念都不會念了。至少他們的抑揚頓挫還頑強地留在英語裡,說起話來字和字之間總要頓、一、下。
她回到書店,跑上樓,經過客房――每間房一張四柱大床,鋪著乾草床墊,一旁的五斗櫃散發薰衣草香,廚房的地板上留著過往爐灶的痕跡。那圈褐色汙漬就是以前擺爐灶的地方。浴室裡雖然有古典的獅爪浴缸,便所的馬桶卻是木頭座椅,沖水時要拉一條冰冷的鏈子,涓涓細流才會從水箱裡流出來。
杜麗放著客房不住,偏要住閣樓。她趕走蜘蛛,丟掉留聲機和壞掉的家具,刷洗裂開的地板,把舷窗擦到近乎透明。她利用閣樓的樓梯將雙人床的床墊推上去,鋪在閣樓地板上。入夜後就睡在屋椽下,早上起床鼻尖總一片冰涼。
晨間散步回來,衣服還是溼的,她脫下來,裸身站在窗邊,從街上只看得見她的臉。她喜歡這樣沒有窗簾。這裡地勢高,別人也偷窺不到。地板上堆著一疊她的衣物和一個大帆布包,可以裝進她所有的東西。這就是她擁有的一切。十年下來,值錢的東西都丟盡了。
她換好衣服,下樓回到書店,算好找零,將昨天的進帳輸入電腦(花不到她幾分鐘),把休息中╱營業中的牌子翻面,打開上鎖的大門。雖然書店十點才開,但她總是早到。弗格跟她相反,總是晚到。
「塞車,」他會這樣解釋,然後鬆開用下巴夾著的報紙,把卡布奇諾放上吧檯。他從家裡走到「世界盡頭」只要四分鐘,所以「塞車」的意思是在蒙娜麗莎咖啡館排隊。他習慣早上帶一杯熱飲和一份冰冷的報刊,每天買的報刊都不一樣,兩個人會輪流讀,下午討論。在那之前(至少到中午為止),他盡量不開口胡扯,只躲在書架後面。喝咖啡的「嘶嘶――」聲會洩漏他的位置。若不是在「地理」,就是在「政治思想」。
像這樣安靜的早晨,她會閱讀最新著迷的事物,翻翻顧客推薦的書,撢撢灰塵。以前她還會用鍛鐵餐桌上的錄音機放幾卷錄音帶來聽。那都是她聽了好幾年的老歌。但這些錄音帶已經不在了。幾個禮拜前來了一對陰陽怪氣的老夫婦,兩個人穿著一模一樣的羽絨大衣,簡直分不出來當年誰是新郎誰是新娘。他們一前一後逛了一圈,回到門口的鍛鐵餐桌,其中一人拿起杜麗的錄音帶。「露營車裡應該放點什麼來聽聽。」
「這些不賣。」弗格說。
\「可以賣,」杜麗插嘴。到了這個節骨眼,有錢當然要賺。「不先看看裡面是什麼嗎?」
「我比較喜歡聽音樂。什麼音樂都好。」
「你比較喜歡音樂?所以比起有聲書,你更喜歡音樂?」
「比起講話,更喜歡音樂。」
他們講定每卷錄音帶五十便士,老夫婦數著硬幣,杜麗盯著錄音帶,上頭寫著「鄧大2000精選」。那是多年前的男友鄧肯・麥格羅瑞錄給她的,標題後面還有冗長的註腳,附註裡頭有哪些人的歌。包括費歐娜•艾波、林納•史金納、多莉•艾莫絲、巴布•狄倫、清水合唱團、湯姆•韋茨。寫到後面空間不夠,字越寫越小,星號旁邊又加上星號。卡帶還沒賣出去,杜麗就後悔了,但她不肯改變心意。那是幾個禮拜以前的事。多想無益。「要不要聽聽廣播?」她問弗格,順便還他小說。
他走到電腦後面播BBC Radio 4。「妳覺得好看嗎?」他問:「根本垃圾,我覺得。」
「超難看。那你幹嘛推薦給我?」
「因為實在太難看,所以我想,一定要讓杜麗看一看。」
「全世界只有你會推薦別人看你討厭的書。」
「等一下,」他小碎步跑開,聲音從書架後面傳出來,有些被廣播蓋住。「如果上一本妳不喜歡,」他喊道:「那這本妳一定要看一看。」
「裡面有吹薩克斯風的外星人嗎?」她問:「如果裡面有會吹薩克斯風的外星人,或是任何會樂器的外星人,或是任何不會樂器的外星人――只要有外星人就不准拿來給我。」
「這樣有點霸道吧。」他拿著一本平裝書走回來。
「好吧,我不禁止你。但我問最後一次――有外星人?」
「沒有外星人,」他保證,然後加上一句。「但可能有半獸人。」
「所以是有半獸人還是沒有半獸人?」
「有半獸人。」
身為雇員,弗格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看店,好讓她外出去買三明治。除此之外,他的貢獻少到無法計量。但她不想一個人經營。「世界盡頭」根本不賺錢,他的薪水是她貼錢付的。她的積蓄不多,而且日漸減少,再過幾年就要破產,但她卻不耐煩地看著戶頭餘額,迫不及待要變成窮光蛋。這裡是她有生以來住過最久的地方,她甩不開那股想失去這裡的衝動。
弗格這種人跟她截然不同,他待的地方形塑了大部分的他。他離不開這裡――離不開這個可以在 Google Earth上找到的村子(他好喜歡把Google Earth從巴黎轉到凱諾鎮,然後一直拉近、拉近,直到看見「世界盡頭」的屋頂。)他說,之所以待在這裡是因為這個村子是「la pièce de résistance. 」這種說法很厚臉皮。他明明是怕人家說話。十五歲那年夏天,他家裡遭逢事故,哥哥出了車禍,腰部以下癱瘓,因為一筆旅館簽單,父親外遇被發現;母親受不了,崩潰了。父親離開,家裡走樣,全靠弗格維繫。四年前,他差點步入禮堂,但女友去倫敦搞劇場,在那裡遇見了新的人。他們一直保持連絡,直到她寄來寶寶的照片。「點開信件夾裡的寶寶照片,」弗格說:「就像看見朋友跟你揮手告別。」他和前女友偶爾會傳訊息,對方邀他去倫敦,他會回說:「我想去啊――什麼時候?」她幾個月後才回傳。而他連她長什麼樣都記不得了。她的臉書顯示圖是一張寶寶的照片。
他困在凱諾鎮,想像自己的平行人生。在另一個時空裡,他在德倫大學取得法國文學學士,又去劍橋念了碩士,再到巴黎做兩年研究,住在左岸(他管那地方叫「西岸」)的閣樓裡。在他人格深處堅信自己生錯了地方。他和他朋友的層次比凱諾鎮高很多,之所以遭逢種種波折,都怪這個地方太落後。每個月會有一天,他上班的情緒極度黑暗。除此之外,他開朗到令人動容。
「你覺得自己比較像英國人還是威爾斯人?」她問他。
「我像法國人,」他回答。「妳呢?覺得自己像法國人嗎?」
「哪裡像了?我一點也不法國。」
「那是像英國嘍?」
「我不是英國人。」
「那當威爾斯人好了?」
「我不是威爾斯人。你不是早就知道。」
「我們就像消失的部落,我們這些威爾斯人,」他喃喃自語道。「沒有傳統,沒有權力,雖然很殘酷,不過是實話。我們只有一顆橡實的哀愁,」他一面說一面把放大鏡貼在眼眶上,「不經意被瞥見的tristesse 像一扇門,通往屋裡外人不得進入的小房間。」
「你今天非常詩情畫意啊,弗格。」
「你往門裡匆匆一瞥,」他繼續往下說,誤把她的挖苦當鼓勵――「一顆橡實的哀愁。」他很得意自己造了這麼個新詞,一邊掛在嘴上一邊走向「海盜・走私・叛亂」,整理書去。
中午時分,第一位客人上門,是一位常客,但稱不上是顧客,她把「世界盡頭」當作展示間,買書都上網買。這種行為日漸普遍,那些在筆記本上記下價錢和ISBN的都是這樣,有些甚至大大方方用智慧型手機上網比價,然後一手搭著門把,一邊感慨好書店剩不到幾家。杜麗並不因此憤慨,潮流不會因為你擺手而停駐。她把賣書當作寒暑假。真正令她氣餒的是,書架上千斤重的書影響力微乎其微,不論裡頭內容多有價值、多有想法。這些書過的是老人般的生活,世人少有耐心聽他們把話說完。
\上門買書的人少之又少,來賣書的倒是源源不絕。近日大家都在清書架。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她有(多少)錢可以買,而是她有多少空間可以擺。她個人有興趣的是那些經典的食譜書,尤其是裡頭還有給小妞兒一些過時建議的那種。例如一八六一年出版的《比頓夫人的持家寶典》,或是吉茵珂絲・摩根和茱蒂・派瑞合著的《單身女子平底鍋》。她也買了一櫃動物學的書,近日又增加了野牛的悲慘歷史、珍禽的珍本書和自然寫真巨冊。就跟那些茶几書一樣,她總是買了才納悶要擺哪兒。
第一個上門買書的是湯瑪士先生。他五十幾快六十,有一堆會說威爾斯語的孫子,每個月會來「世界盡頭」一次。在他念書的年代,教育被看成是不肯下田做活的可惡藉口,這種態度造就了兩種人:一種不屑念書,一種則敬書本如鬼神。湯瑪士先生鼻尖有疤,生著一副正直閒人的面孔,身上永遠穿一件手織羊毛衫,他是令人尊敬的刻苦自學者。但他不喜歡講這些,總會打斷她的攀談,站在鍛鐵餐桌前,一手一本書,彷彿圖書館櫃檯前的孩子那樣。(她始終摸不透他選書的喜好。這天選的是跟波耳戰爭歷史有關的書和《愛麗絲夢遊仙境》。)
「這些就夠了嗎,湯瑪士先生?」
「不用了,謝謝。」
「需要幫你找什麼嗎?」
「不用了,謝謝。」
「謝謝光臨,下次見。」
「很好很好。很該走了。」
門上的鈴鐺在他身後響起,店裡瀰漫學生湧入之前的寧靜。這些學生不是狼吞虎嚥的讀者,而是順手牽羊的小竊賊,來她店裡小試身手。看他們左瞧右瞧的鬼祟模樣,彷彿是扒竊這行的始作俑者。真厲害,小小的書包竟然可以塞這麼多東西。偶爾她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除非在羅伯斯路的垃圾桶裡發現被偷走的書,才會制止罪犯再次突襲,抓到門邊訓話兼送客。少數幾個沒規矩的,她會字斟句酌地把他們罵到臭頭。有一個臉皮特別厚,離開時還踹門,一邊倒著走一邊朝她比中指,結果(想到就覺得爽)跌到水窪裡去了。
她看了看時間――晚上要上課。「介意我……」
「別說了別說了,」弗格回答。「快走吧。」
自從來到凱諾鎮,她就開始瘋狂學東西。又是縫紉、又是居家修理(出乎意料有趣)、又是音樂。有一陣子,她每個禮拜二晚上開車到卡地夫學畫。她畫的是人體畫,包括炭筆、油畫、壓克力畫,每一種媒材都證明她毫無天分。畫出來的手臂總是比腿長,耳朵像茶盤,水果像籃球。雖然畫得很糟,但杜麗喜歡。苦學一陣之後倒也越畫越好了。
「有教畫鼻子的課嗎,」她問老師,對方是一位易怒的失意雕刻家。
「什麼?」
「可以教我畫鼻子嗎?」
「什麼?」
一期課程上完,她看來看去,實在想不出理由保留任何一幅畫,但還是載了一幅靜物畫回家。名字是「蘋果――至少我是這麼想的」。她把畫釘在閣樓裡,雖然醜得可笑,但一看到就開心。
偶爾也有同學邀她喝一杯、聊聊天。波露剛離婚,在赫里福德市學居家修理。她問杜麗除了經營書店還做些什麼,聽她說她天天健行。「我也該四處走走,」波麗說:「生完孩子就懶了。」一天早上,波麗到「世界盡頭」來,出於禮貌買了一本羅曼史小說,然後搭杜麗的車到嵐托尼修道院走走。這位新朋友才走到山腳就跟不上了,中間一整段都在咬牙苦撐。杜麗等在山頂,一面欣賞鄉村風光,遠遠望見一個只有豆大的人影,拖著沉重的腳步越走越近,展開便成一名女子的模樣。「穿――」咻――「穿錯――」咻――「穿錯鞋子了!」
「從這裡開始就是平路。」杜麗邊說邊沿著山脊走了起來。
「妳走――」咻――「好――」咻――「快――」
「有那麼快嗎?」
事後波露向她道謝,從此再也不說要跟了。杜麗多少是故意的。交朋友需要供出過往人生。人的過往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有人探問――就是這些人規定人一定要有過往。一個人,沒有過往也是可以的。
就是因為這樣,她和弗格處得很愉快。他接受她的迂迴,從不刺探。
「晚上學什麼?」他問。
她舉起手中的烏克麗麗。
「雖然很殘酷,不過是實話――我跟烏克麗麗的作品不熟,」他說:「妳怎麼會想學這個?」
「某天突發奇想。」她回答。「鎖門的時候順便把誠實樂捐箱收進來。」
開車到蒙茅斯鎮的路上,雨傾盆而下。到了老師家,她從車裡衝出來,把樂譜和烏克麗麗夾在襯衫底下。老師應她的要求教了《威廉泰爾序曲》,她彈一段,老師伴奏一段,然後師生交替。多開心啊!音符一步步發展成樂句,五線譜上的豆芽菜流瀉成樂曲,一八二八年寫下的音符,演奏了世世代代!真是太令人興奮了,有幾次她甚至興奮到彈不下去。
她一路走走停停,飛車回家,腳在油門踏板上打節拍,扯開喉嚨高唱。「噠噠啦――噠噠啦――噠啦噠噠!」擋在乘客座窗口的塑膠布劈哩啪啦替她伴奏。她開進「世界盡頭」對面的停車場,四處繞來繞去找車位。這裡晚上都停滿「屠夫之鉤」主顧的車。
要不要繞去喝一杯助興?她漫步在羅伯斯路上,離「屠夫之鉤」越近,喧鬧談笑聲就越響。一群讓太陽、灰塵、香菸弄得灰頭土臉的勞工坐在戶外野餐桌旁,手裡拿著摻水啤酒,眼睛打量著參加告別單身派對的姐妹淘。她們踩著高跟鞋,身材豐腴,腳踝刺青,大腿上起了雞皮疙瘩,下垂的奶子給內衣鋼架束得鼓起來。對街是一家軍團酒吧,專收從外地回來的退役軍人,從伊拉克或阿富汗退役的小夥子射飛鏢射膩了,就陰鬱地看著對街的女孩望著打翻的蘋果酒笑得花枝亂顫。
杜麗從兩家酒吧之間走過,兩旁的男子鷹視虎睨,看她一頭短髮、嘴脣蒼白、打扮中性,便對她視而不見。近來若有人向她示好,她就疑心對方沒志氣或發花痴。倘若真的踏進「屠夫之鉤」,一定會撞見不少發花痴的色鬼。雖然跟喝醉的色胚玩玩也不錯,但是村子就這麼大,難保日後撞見自己鑄下的大錯。還是回家吧。今夜她只想要一杯微醺。廚房裡就有一瓶剛開的黑皮諾葡萄酒。
她斟得太滿了,嘴脣噘上杯緣,咕嚕咕嚕喝到剩七分滿,小口小口吃起乳酪配餅乾,嘴裡哼著《威廉泰爾序曲》,嘴脣跟葡萄酒同一個顏色。太不可思議了,這酒!過了某個年齡――大約是二十六吧?當最後一點青春的浮躁散去,一股壓力在她體內日漸成形,碰撞著她自身存在的邊界,直到初次啜飲那夜,她膨脹了,放鬆了,在思緒裡飄起來,飄到時間之外。她一手支著額頭,從上了閂的窗戶望著綿延到凱諾鎮盡頭的農田,此時一片漆黑。她後退一步,看著窗戶上自己和廚房的倒影,酒杯隨著一分一秒變空。
她下了樓,腳步微醺地走過昏暗的書店,只要一伸手,就能觸碰到許多崇高的心靈。她大可把他們從書架上叫起來(不論何時,他們都比她更機敏),吩咐他們開始動作,去邂逅跟她一樣能感知的靈魂――只是更敏銳一些。但今晚誘惑著她的是電腦。她把鍵盤兜在膝上,打了個顫,電腦眨眨眼,呼呼運轉起來,圖示一個個住在桌面上,螢幕照亮她的臉。杜麗向來不碰電腦,因為電腦讓她想起保羅。她逃避得很成功,因為她的生活全無接線。她旅行過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換過一個工作又一個工作,專挑不必具備科技技術的職位。沒有電腦的生活過久了,外頭的數位喧囂就更令她迷惘。
然而,「世界盡頭」除了帶給她一綑又一綑的紙,也帶來了幾片微晶片,就在這臺笨重的老桌機裡。它是這家店的資深住民,今年四歲。弗格教她輸入帳目,除此之外還堅持教她上網。他會一面對網路的神通廣大歌功頌德,一面搜尋她的名字給她看――結果卻讓他洩氣了。竟然一筆資料也沒有。
過去一年多來,杜麗能不碰這臺桌機就不碰,頂多上網搜尋「烏克麗麗」,但險些被排山倒海而來的搜尋筆數嚇死。她開始一點一點探索網路世界,幾個鐘頭就這樣消失。就像黑洞一樣。網路自行產生重力,把光和時間都吸進去。貓咪彈鋼琴,奶子亂晃,生殖器外露,陌生人詆毀陌生人。因為沒有目光接觸,網路世界上演著千奇百怪的戲碼,包括她最新的嗜好:潛伏在其中尋覓過往。
幾個禮拜前,她開始搜尋人名。舊的人名。包括失聯的朋友、以前的老師、學校的同學、幾年前在異國城市萍水相逢的朋友。她在陰鬱的網路世界偷窺他們的生活,拼湊他們的人生:念什麼大學、在哪裡工作、跟誰結婚、參加哪些活動、興趣是什麼。LinkedIn上有著他們光鮮亮麗的職涯起點:試用期員工――地區經理――副總裁。然後莫名其妙轉為自由業。臉書的「居住地」則冒出意想不到的地點,奧斯陸或是河內或是利馬。如果他們始終保持聯繫,畢業、就業、成家只不過是漸進的歷程,用不著大驚小怪。但網路上的簡歷把人生的累積變成跳躍的進程,昨日的學童瞬間變成頭髮灰白的家長。
真是太奇怪了。告別了這麼多人、這麼多地方,如今卻一心一意放在這上頭。他們對她肯定漠不關心。杜麗從不聯繫這些被她窺視的人,只用假名瑪蒂達・奧斯妥波利在網路上人肉搜尋。瑪蒂達是她真正的名字,奧斯妥波利則是以前一位朋友的姓。
這些懷舊的尋覓總在幾杯黃湯下肚後令她感到滿足,但也令她不安,彷彿有根長湯匙伸到她體內舀呀舀、攪呀攪。不像書本,網路沒有最終回,只有永無止境,一個連一個,讓她感到疲憊,讓她緊繃,讓她無眠。
該關機了。該去睡了。盯著屋椽,想想晚上的烏克麗麗課。如果閉著眼睛想像指板,大腦會趁她睡覺時練習彈奏嗎?
她半站著,叫醒電腦,看看是否每按一下滑鼠都能帶給她滿足感。螢幕左上方出現一面小旗,是臉書的交友邀請。因為她用的是假名,所以加她朋友的都是潛水的怪胎。她點開邀請,打算拒絕。
沒想到那卻是她認得的名字:鄧肯・麥格羅瑞。
杜麗離開電腦,心神不寧地走進最近的走道,一邊走一邊輕叩架上的書。她跟鄧肯好幾年沒連絡了。他是怎麼找到她的?她口乾舌燥地回到桌機前,手指懸在滑鼠按鍵上。再讀一遍他的名字。按下確定。過了一會兒,他丟訊息給她。「找妳找得急死了。想跟妳談談妳爸的事!!!」
她握緊溼冷的手,在襯衫上揩了揩。她爸?哪一個?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