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差的贈禮
| 作者 | 黃錦樹 |
|---|---|
| 出版社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 商品描述 | 時差的贈禮: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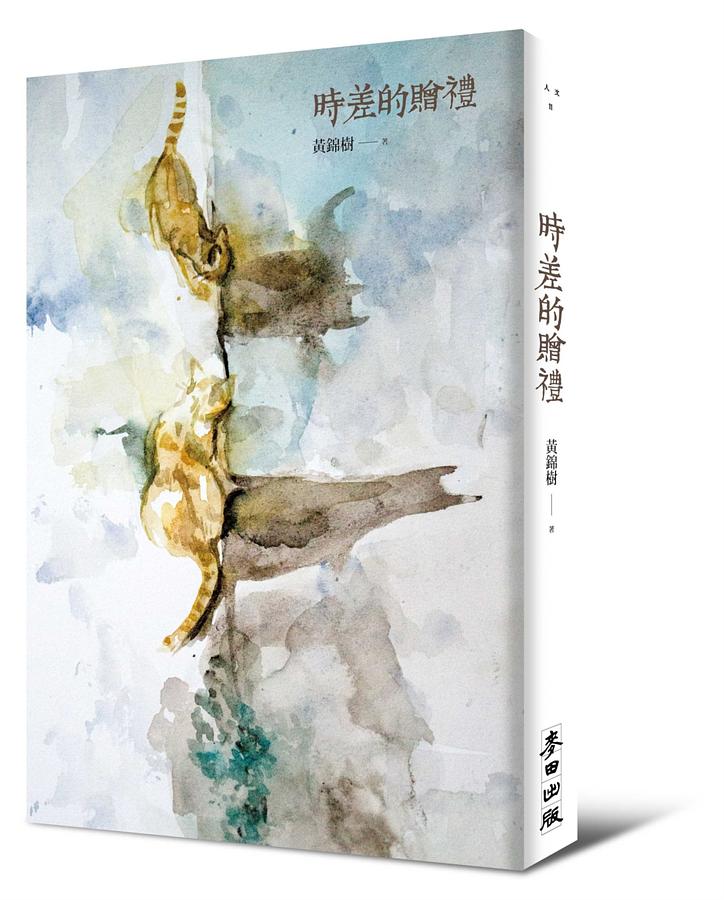
| 作者 | 黃錦樹 |
|---|---|
| 出版社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 商品描述 | 時差的贈禮: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 |
內容簡介 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 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 / 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我而言,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 全書共分四輯。 輯一,書寫傷逝,向師友前輩告別或致意,都是寫於近年。最後兩篇是關涉這三年來猝然臨身的、醫生說「其實沒有療程」的疾病。 輯二,收錄多篇序文及書評。〈最後的豬籠草〉是為張貴興的《猴杯》寫的簡短解說;〈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是為出版小說選而撰寫的向華社募款公告,結果所得為零,因此是一份相當有紀念價值的歷史文獻……幾篇書評是為《聯合文學》雙月書評專欄而寫的,刻意挑選馬華文學作品,是因為比較少人會去討論它們。 輯三,新舊文各居一半。〈立錐無地〉涉及的是種族政治下大馬華社的結構性困境,〈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意在反思,以大馬的環境,需要一個國學系、漢學系式的中文系嗎?還是像馬來半島的食物,提供一個混雜式的文化教養,以比較文學為根基,意在強化在地研究和寫作,「傳統中國文學」只保留最必要的部分。〈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可說是「馬華文藝獨特性」的當代表述,一個非革命文學的版本,〈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主要談理論常識。 輯四,關涉馬華文學的「沒有論述」,涉及幾場對話。與朱宥勳的紙上對談,催生了本書的書名;與「假文青」的討論催生了注定不會像季風那麼恆久的《季風帶》;而為什麼沒有論述,是個老問題。因為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或許只有離開它方能抵達它。為了抵達你必須離開。〈致新人〉是個意料之外的收穫,原來學院裡還有一些不錯的研究生繼續在思考馬華文學問題(高嘉謙、張惠思、許德發等功不可沒),那終歸是個希望的種子。 / 關於書名,幾經考慮,從「沙上的足跡」、「時差的贈禮」到「燒芭餘話」。後來想想,現在的我火氣也大得很,那又怎樣?寫著寫著突然醒悟:如果不是那年大火燒芭,如果不是那場大混戰,我對馬華文學的介入或許不會那麼深遠、持久。換言之,那之後我的所有論述,都可說是「燒芭餘話」。燒芭只是個起點,接下來的工作才重要。總要種一點什麼。不能老是以欠缺「文化資本」來合理化不做為,或玩世不恭,以文為戲,而消耗掉可能寫出佳作的時光。 書名因而重拾回「時差的贈禮」,也就是「給自己們」。至於種籽會不會發芽?天曉得。我曾把我們的寫作教學工作比擬為在水泥地上播種,有裂縫又剛好有水,種籽才可能發芽。那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們自己就是從水泥裂縫中擠出來、傷痕累累的長大的。 ——黃錦樹
作者介紹 黃錦樹黃錦樹,馬來西亞華裔,1967年生。1986年來台求學,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清華大學中國文學博士。1996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獲多種文學獎。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
產品目錄 自序 告別與祝福 輯一,荷盡初冬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同鄉會 遺作與遺產 荷盡已無擎雨蓋——一個「盡頭」的故事 在冷藏的年代 老麥和他的流放 木已拱——我們的《百年孤寂》 別一個盗火者 在欉熟 夢與序 輯二,自己的文學自己搞 「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序張錦忠《時光如此遙遠》 華馬小說七十年徵求認養 辭謝南方學院大學邀請擔任《蕉風》名譽編輯顧問函 不錯與夠好 叔輩的故事 最後的豬籠草 腳影戲,或無頭雞的鳴叫 愛蜜莉之謎 真正的文學的感覺 缺席與在場 政治的,太過政治的 後革命年代的馬共小說 文學的犀鳥之鄉――序梁放小說《臘月斜陽》 回家的路――序陳建榮先生《歲月的回眸》 文學檔案,現代主義,豆糜--序杜忠全《文字新語》 詩的空間――序林婉文《我和那個叫貓的少年睡過了》 化為石頭,化為文字——讀黃琦旺散文集《褪色》 文學的工作 「我生來不是」――讀馬尼尼為《沒有大路》 輯三,一個微小的心意 牆上貼著的中國字 老輩知識人的傷心之言 附錄 張景雲〈立錐無地〉 我們的演化 我們需要一個怎樣的中文系? 文學課 中國性,或存在的歷史具體性——回應〈窗外的他者〉 互文性,寫作,與文學教養 大背景,小產業,歷史墳場 一個微小的心意――《雨》跋 南方以南――《雨》大陸版序 廣州馬華文學研討會後 甲午歲末小雜感 我的馬華文學 旅行與時差 輯四、時差的贈禮 如何/何發動一場文學論戰?——與朱宥勳對談一 在我們的年代,還有鄉土文學嗎?——與朱宥勳對談二 論述者為甚麼要創作/創作者為甚麼要論述??--與朱宥勳對談三 給自己們——-時差的贈禮--與朱宥勳對談四 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 東馬觀點,西馬觀點――關於「馬華文學」 「評論文字之匱乏」 關於「沒有論述」--回應林韋地 關於「論述」--回應林韋地(續) 〈燒芭餘話〉引言 也算流亡?——跋〈異鄉的內在流離者——訪問黃錦樹學長〉 致新人――「異代新聲」研討會後
| 書名 / | 時差的贈禮 |
|---|---|
| 作者 / | 黃錦樹 |
| 簡介 / | 時差的贈禮: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馬華文學是一支作品、作者、讀者三重缺席的文學,它的存在本身是反諷的。對 |
| 出版社 /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
| ISBN13 / | 9789863447023 |
| ISBN10 / | 9863447021 |
| EAN / | 9789863447023 |
| 誠品26碼 / | 2681820671007 |
| 頁數 / | 336 |
| 注音版 / | 否 |
| 裝訂 / | P:平裝 |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 尺寸 / | 21X14.8CM |
| 級別 / | N:無 |
最佳賣點 : 本書是黃錦樹近幾年的雜文集結。
可視為黃錦樹對文學、尤其是馬華文學的關懷之作。
內文 :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夥伴」(consociates)是實際相遇的個人,是在日常生活中相會於某地的人。因此,他們不僅共享一個時間團體,也共享一個空間群團—無論它們是多麼短暫和表面。他們至少最低程度地互相「涉足對方的個人生活史」,他們至少暫時地「一塊兒長大」。……只要愛情延續,情人就是夥伴,直到他們分手;或者是朋友,直到他們翻臉。……正是多少具有這類延續性的關係的、為了某種長期目標而走到一起的人,而不是僅有零星或偶然關係的人,構成了這個類別的核心。
「同代」(contemporaries)是一個時間群團,而非空間群團:他們生活在(或多或少)同一個歷史時期內,互相之間具有經常是非常淡薄的社會關係,但他們按照慣例互不謀面。……他們是透過互相之間典型行為模式進行符號系統表述的一套普遍假設來聯繫的。……個人所涉及的從情人到偶遇者的夥伴關係系列,就在這裡延伸,直到社會紐帶變為完全的無名、標準化,和可置換狀態。
—格爾茲,〈巴厘的人、時間、行為〉
前代。後代。……(略)
「同時代人的非同時代性」。不同代生活在同一時間,但體驗中的時間是唯一真實的時間,因此他們實際上生活在事實上相當不同的主觀時代中。
—曼海姆,〈代問題〉
我一九八六年深秋到台灣時,並不知道歷史即將翻過新的一頁,長長的一章戒嚴史將在次年畫下句點。又一年,民國最後的強人「建豐同志」(《北平無戰事》裡沒現過身的領導,蔣經國的字)過世。前此,我們從電視上看到的他,是被糖尿病折磨得浮腫,沉坐在輪椅上的衰老模樣,和那被他派黑道殺手去幹掉的江南在《蔣經國傳》勾勒的陰狠毒辣神祕形象完全不一樣。戒嚴的解除,開放到中國探親,等於公開承認反共復國之夢從此畫下句點。也許從那時開始,民國歷史就進入它自身倒數著的剩餘時間。
我們這一世代,身在大馬以公平分配為名、方便馬來權貴橫徵暴歛的新經濟政策的馬哈迪時代,對大馬的認同卻是毋庸置疑的。踩著僑生輸送帶來台的我,在激烈本土化的背景裡,對這預設了中國認同的身分也極不耐煩。那時並不知道,那中國其實是民國,我們因沒有更好的選擇而被捲進他方歷史浪潮的浮漚裡。那種種看來刺眼的民國標誌,老蔣的銅像、「國父」遺像、看電影前必須起立等待「吾黨所宗」的國歌唱完;得上最無聊的軍訓課,誦讀那從周公孔子始、「蔣公」為句點的噁心厚顏的道統史。其中一個暑假,還得參加大魚大肉的海青會—那是軍事訓練的少爺版、兒戲化的模仿,和作為同世代台灣男生成年禮的兵役是兩回事。因此我其實並不是此間「五年級」的同代人,在場而不在場。
僑生,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烙印(stigma)、標記,但有時確也是個污名(戈夫曼,《污名》)—成績墊底的、靠加分進來的、說話怪腔怪調、讀音錯舛、滿紙錯別字、住在樹上的—在台灣本土自我建構的年代,「僑生」再自然不過的,也被劃入敵人的陣營。因此,八○後留台的大馬青年,也努力建構屬於他們的、大馬的本土自我。歷史的閱讀是當務之急的補課,從華人史、東南亞史到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史,圖景漸漸拼湊起來時,竟然大半輩子過去了;為民國斜陽寫下個人版悼詞的我,已是大馬的異國之人。在此間交疊著差異歷史經驗的「作為過去的未來」的(走向一種更純粹的民族國家的)現實裡,新舊國族認同幽靈的角力,投影在文學的牆上,是殺氣騰騰的皮影戲。
僑生這標記卸除後,那標誌著外的印記反而被更其存有論化,成了身分認同本身,一種沒有的有,一種空符號。字輩、年級云云,對我來說也是如此。也很少人會注意到,那兩者之間其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可以自由轉換—對我而言,箇中難免有時差—貨幣的轉換況且有匯差。我也不敢說我的經驗有多大普遍性。但我們這些寫作的留台人(自李永平〔一九四七—二○一八〕以降),和台灣—民國的主流文壇、各個不同的水滸山寨都是疏離的,都是孤鳥,懸浮之島,或孤狼,鮮少應酬,彼此之間也很少往來,泰半「絕對孤獨無情」的「自己的文學自己搞」,好處是可免於一些無聊的江湖摩擦。也因為作品反正沒市場,不會有太多關注,就不必做多餘的努力,不必特別去巴結;不想見的人也可不必見,不得已見著、不得不說上幾句時,也可僅僅談談天氣和交通狀況。
因此,「六字輩」小說家的兩場重要的葬禮,我都無緣參與。影響力巨大,但成就可能被過高評估的邱妙津(一九六九—一九九五)和袁哲生(一九六六—二○○四)年歲略大及略小於我。前者我根本沒見過,後者也只有數面之緣,但他們猶活生生的活在同代人(四—七字輩)的記憶裡,有過一些接觸,甚至曾經是工作上的夥伴,或者有著師生關係,兀自記得他的笑語神情。
這世代我比較熟的,也就是個駱以軍。但那也是一九九九年的事了,其時我們都已年逾而立。
最近黃崇凱提醒,我在不同的隨筆裡,我似乎都會戮一下長我十歲的張大春,「會讓人以為你很討厭他」。最近回應一位老朋友的質疑,為一位青年朋友辯解時,也舉我一九九八年的論文〈謊言的技術與真理的技藝〉為例,我不是因為張某罵我我才批判他(那時他也不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而是他的作品、文論、經常在文學獎決審時的發言,以及那一大批不斷為他的作品歡呼解釋(以所謂的「後現代主義」)的名流學者的論述中共同展現的某種價值趨勢,讓我深不以然(也許就因為我是個局外人)。但台灣「五年級生」多為其弟子門生,深受濡染(或霸凌)。那是個價值層面的爭辯,也涉及小說寫作的一些根本問題。但即便批判了那個名字,那作者—功能兀自發揮著影響(他畢竟調度了許多西方當代文學資源,有其相對的正當性),被敲散、化為液體之後,仍一直向下、向繼起的世代滲透。那是養分,但那養分裡也可能有毒素。每個世代都要清理前代留下來的遺產與債務。世代之間的競爭與愛恨,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
有一回,五年級某大腕轉述四年級某大咖酒後對某出版界大老之狂言:「滅掉五年級,我們就可繼續吃香喝辣二十年。」我的私訊回覆極簡:「滅掉?我們兩個他就過不去了。」
但我們在文學場域裡其實並無權勢。在我,能做的也僅僅是論述而已。
年初,大馬的朋友在為花蹤籌辦系列暖身文學活動時,注意到近年在網路上相當活躍的「七年級∕八字輩」的朱宥勳(一九八六—),決定邀他去演講。「在逃詩人」透過臉書和我商量,要找出堪與匹敵的大馬同世代文青與彼座談,清點之後,結論卻相當悲傷:一個也沒有。「同代沒人有論述能力,評論早就產生斷層了。」他說。年歲比他大一點的呢,也沒有,最終還是七字輩∕六年級的大姊頭黎紫書(一九七一—)親自出馬。那沒有論述(能力)的一代,「只是天真地著力於開創自己的時代」(〈江湖催人老〉,《聯副》,二○一五年十一月四日),當然也各有建樹。然而,為什麼在華社有了幾間自己的大學、有幾個自己的中文系多年以後—在中國留學之路廣開,許多人花盡血汗儲蓄取得博碩士學位歸國之後,文學的論述還是那麼貧瘠?
其實,一九三○—一九五○年之間的世代(不乏有「留台」且取得博士學位者),也談不上有什麼論述。左傾的,多搬屍於中國左翼(「搬屍」不是我的惡言,是時人用語,大馬雜文好用惡言毒語);嘗試借鏡於港台或四○年代中國現代主義,以爭取文學的自律的,已經是空谷足音了。比我們更年輕的世代,也許不會(或無意)記得,在「人民需要文學」的年代,「因為喜歡文學而寫作」是政治不正確,會被用惡毒的話公開批判圍剿的。甚至時至今日,還有人昏庸的召喚昔日的毒草精神(莊華興,〈馬華創作的思想基調〉,http://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二○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沒有文學論述,可能是因為已經沒有東西需要捍衛;馬華文學已經沒有敵人?文學作品不是自明的,尤其比較複雜的作品,都需要論述的闡發,需要知音之談(真正有眼力的讀者並不多);那頗有益於教學,及文學記憶的傳承。寫作的人有時也需要「畏友」,在一片阿諛奉承聲中,獻上幾聲言之有物的鴉鳴。提醒自滿的寫作者,那被誤認做太陽的,其實不過是盞稍大的燈,我們其實兀自在暗夜裡摸索著各自的路。
倘就馬華文壇(包括留台這塊)而言,沒有文學論述其實是歷史的常態,作品的沉沒、作者的被遺忘(生平資料殘缺),也一直是歷史常態。
更悲哀的是,沒有論述可能不是最糟的,惡意的、愚蠢的論述還要更糟。
字輩(大馬)、年級(台灣)的世代劃分,當然是極不科學,也不能太當真的。十進位制,始於○終於九,因此七年級頭的黎紫書只比我小四歲,而她只比六年級尾端的鍾怡雯、陳大為小兩歲。倘是在唸小學或中學,這年歲的差距似乎不小;年過四十之後,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
越過了那條年歲的換日線,人生就走入秋日午後的下半場了。
二○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歲次乙未,初冬小雪
初冬,節氣在小雪之前的十一月中旬,我給昔年台大中文系的老師林麗真先生寄了本甫出版的隨筆集《火笑了》。附了短箋,說明贈書緣由—將近三十年前,修習林老師的大一國文時,曾寫了篇作文〈我要蹺課〉。用時下的俗語來說,是篇「靠北文」,但也是個行動宣言,我真的蹺課去了。年歲漸長、我自己也當了多年中文系的老師後,心裡不免有愧,贈書是為了致歉,感念林老師當年的寬容,《火笑了》也許比我寫過的任何書都適合這樣的目的。幾天後,收到林老師的簡短覆函,客氣的問,哪天她南下日月潭,是不是約個時間喝茶。在我寫著一樣簡短的回函時,突然就接獲周鳳五老師過世的消息。
當年,林老師的課其實上得很認真。一九八六年底,機械系的朋友(同年進入台大的高中同班同學)通報說,他們的大一國文老師口才一流,班上那些對古文一點都不感興趣的同學,都聽得津津有味。我去旁聽了一回之後,就決定蹺課去旁聽了。和所有「非好學生」類似,上課的具體內容都不記得了,只記得一些課餘零碎的邊角。周老師其實早就在實施當下流行的「翻轉教學了」—他常讓那些唸工科的大孩子上台憑各自準備的材料講解選文的注釋、做白話翻譯,並嘗試講解,他在一旁隨時評議修正;若干戲劇場面,更要求一組組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讓他們進到那古代的情境裡。他是導演,且負責旁白,而又擅長以幽默風趣的口吻不慌不忙的講著遠古時代的故事,因此學生臉上常帶笑容,課堂時聞笑聲。
他總是髮黑如墨、西裝筆挺的提前到課堂,到同學的座位旁閒聊一會,關心一下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等鐘響了、人差不多到齊了,再走到講台前,翻開書,清一清喉嚨,正式上課。
我因高中後期大量閱讀李敖的著作,累積了不少困惑,大學時逮到機會就拿來問老師(連軍訓課的教官都不放過),有一次甚至帶了本購自舊書攤、封面有洋裸女的《千秋評論》的「王國維之死」專號。周老師對這問題發表了簡短的看法(具體內容我也不記得了,應是認同殉清—畏懼北伐說),但強調李所作所為「不足為訓」。我記得他還談到一個私人的細節,說台大男十一舍○○室在民國□□年(數字我忘了)有一個後來很有名的人搬走,他隨即搬了進去。那個名人就是李敖。說完後,他笑笑的補充說,李敖很聰明,「智商和我差不多。」(多年以後,呂正惠教授側面印證了他的自我評估,呂說周和龔是他見過的台灣中文系兩個最聰明的人。)
那時我且白目的問了周老師的專長領域,他嚴肅的逐一曲著沾了粉筆灰的手指數給我聽他開過的課,古典領域,從尚書、楚辭一直往下數,手指似乎勉強夠用。那時我且不知他書、畫俱佳。
我高中時是理科生,統考(大馬獨中版的聯考)成績最好的科目也都是理科,依正常順序應是唸理工,但我可以預料那會是怎樣的人生,因此進大學時就避開工而拐進農。唸了幾個月,發現那不是我要的,也許受胡亂讀到的雜書影響,對台大的文科也沒多少好感。徬徨著人生不知要往何處走的我,次年會轉入中文系—那其實是個沒有選擇的選擇—和那大半年的旁聽脫離不了干係。
轉入後發現,少壯派老師如柯慶明、林麗真、葉國良、何寄澎、方瑜諸先生都是周老師前後期的同學。但中文系是個冰涼的水潭,我很快就領略到了;完全沒有古典教養背景的我,必修課很少是有興趣的,也很快知道那條路我走不了,況且我有自己的當代要回應(其時只是朦朧的感覺到),但轉系後就沒有退路了。
大三時旁聽周老師的文字學課(大二已修過龍宇純老師的,他退休後換人接手),可能是周老師第一次開那系上必修大課,予人一種全力以赴的莊重感,我的收穫也最多,影響一直到碩士論文(詳我碩論的序,〈讀中文系的人〉,收入《火笑了》)。又一年,選修敦煌學,讀了好些篇敦煌俗文學(〈燕子賦〉之類的俗賦),收穫不大。那年他借調中正、創中文所,我被慫恿去報考,還好沒考上。
敦煌學課的某次休息時間,我看到他靠著走廊的窗,對著中庭枝繁葉茂的老樹和初夏的風,輕輕哼唱一支彼時流行的歌〈隨風而逝〉,唱得相當投入。回應我好奇的目光,他淡淡的提及,一位女性朋友(同學或學妹?)罹癌早逝。聽話中意思,似乎不是一般朋友。那時,我突然問他「老師今年幾歲」,「四十二」,他說。他過世後,從訃聞中得知他一九四七年生,大我足足二十歲。那年就是一九八九年了,我二十二歲。正默默思考馬華文學的困境,反思自己的華人身分,學習寫小說,寫了稚嫩而絕望的〈大卷宗〉,非常苦悶。
那之後許多年一直沒聯絡。我曾在別的文章寫過,一直到一九九六年寒假,我結婚請客時給他寄了喜帖,他有回函但沒出席。暑假時,知悉新成立的暨大中文系在聘人,我寄了履歷過去,身為創系主任的周老師即直接叫我到埔里上班。彼時仍處於工地狀態的暨大,只有林啟屏、高大威,及和我同時以講師聘入的巫雪如寥寥數位老師。同事後才知道巫是周老師高足、多年的助理和祕書,深得其語言文字之學真傳;林也是他的學生,都修過他研究所的高級課程。在台北,也經常和他的一干弟子門生聚餐喝酒,他們都暱稱他為「周公」。但我們相處只有一年,一九九七年暑假,他就回台大去了。彼時他的名言是「事緩則圓」。複雜的人事紛爭,爾虞我詐,學生也分裂成兩派,搞得大家心身俱疲,很不愉快。之後多年沒有往來,一直到去年(二○一四)八月,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臉書留言按讚,方重新以私訊聯繫上。周老師客氣的約我如有到台中,一起吃個飯,說他和埔里的民間友人還有聯絡的。不知不覺,十五年過去了。其後一年,偶爾從臉書看到他含貽弄孫的溫馨畫面,白了頭,老多了。但我自己也老多了。
然後便是葬禮,告別式。
十二月四日,節氣臨近大雪,系上進行著博碩班的入學甄試,恰好沒給我安排工作,故我一早搭車北上。台北比埔里冷多了,還飄著小雨,大風起時身體會不自禁的顫抖。白色花圈布置起來的靈糧堂空間不大,裡外塞滿了黑衣人,但我認得的並不多,一些以為會出席的人也沒見著。會場內外人雖不少,猶不免有冷清之感。寒風裡,靈堂外,只見巫雪如悲不能抑的獨自披髮號啕大哭,一襲黑袍如喪服。
會場內,大小螢幕同時播出周老師的生活照,倒數著他的人生,那是我未曾見過的。年輕時五官比較放鬆,也許二十幾歲就結了婚,俊朗的青年和美麗的妻子;結婚照裡有拄著等身高拐杖的白鬍子張大千,喜孜孜的給新人祝福。似乎很快就當了父親,擁著稚齡孩子時猶一臉青稚。告別式上發送的〈周故教授鳳五先生事略〉裡記述,周先生民國五十九年畢業於台大中文系,取得中文所博士學位及國家文學博士時甫三十一歲,八年間修得碩博士兩學位,相當迅捷;四十歲時升教授(以他的才能,似乎不需那麼長的時間。大學時曾聽過他很節制的吐露一點風聲,當我向他抱怨某君的某門必修課竟然只講朱熹的注而不談文章大義,讓學生自己去瞎子摸象時—某君的名字頗引起他的情緒反應),傑出研究獎、講座教授之類的肯定,更是暮年的事了。以學人而兼才子遭遇尚且如此,多少也反映了中文系這江湖的生態吧。隱約聽說他樹敵無數,亦不知何故也。
古典學厚積薄發,需要長時間的累積。周老師的師長鄭騫先生中年時曾有一篇有趣的文章〈四十之年〉(《永嘉室雜文》,頁三七—四一),寫年屆四十的感慨,列舉古往今來有的人四十以後才寫出重要著作,或建立事功;有的人的生命「簡直是以六十為開始」。文中且評估自己的家族遺傳、長輩年壽,自期「能活滿易掛之數,已經甚為滿足」。六十二歲時,又補記曰「寫這篇文章時我只有三十九歲,不知不覺,竟又混過二十三個年頭,離文中所說『易卦之數』只有兩年了。現在我可不覺得這個數目『甚為滿足』」;過世前兩年又補記曰:「不知不覺又混過了二十二年,今年已八十有四,……眼前一些勉強可以算作『成績』的工作,都是七十歲以後才完成的。……」鄭先生的重要學術專著,多成於七十之後。周先生雖活過了易卦之數,但很多重要的工作可能都沒來得及完成。顯然還需要更多時間。
我算不上周老師的弟子,關注的領域相差太遠。他在埔里時,也常在一旁看他即席揮墨,即興寫字畫魚蝦螃蟹,但那方面我沒天賦,沒能學到什麼。但我對文字考釋的方法論問題頗感興趣,曾問過他出土文字的辨識依據,他只說那如同「猜謎」。偷偷翻閱過若干相關論文後,確有那樣的感覺。我對古文字的興趣一直持續著,但那是詩學、理趣上的,而非古文字學的。可以說僅僅是從窗外走過—門外漢的立場,但古文字成了我小說寫作的養分。
周老師故後,我曾寫信給友人,云:倘非先生,以我的個性和人際關係,以台灣中文學界的生態,我可能會一直找不到一份穩定的工作—更別說是搭上「老賊」﹙舊制,不必經過助理教授那一關﹚的末班車。如果是那樣,多半還是會回馬來西亞去吧。
當年聘我到暨大,他告訴我,理由之一是我應該可以教寫作。他把暨大中文系本科的大一國文規畫為小班制的「閱讀與寫作指導」,我是最早的任課老師之一。應聘之前一年的一九九五年,我以〈魚骸〉得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寄履歷時多半是附進去了,伴隨碩士畢業後發表在《中外文學》的幾篇論文,及以章太炎為議題核心的碩士論文。反諷的是,〈魚骸〉既是對自身華人的文化處境的思考,也是對台大中文系本身絕望封閉氣氛的直接回應。那對古文字的陰鬱想像,多少也淵源於當年的文字學課,與及台大文學院荒涼衰敗的絕望感(近年大翻修過了,還裝了鐵窗和冷氣)。我的碩論原是對中文系的告別,但迄今猶告別不了,甚至還得賴以謀生。
有一回他認真的對我說,能寫作是好的,「那是自我實現」。
九○年代初,我台大畢業後,另一位因我的寫作而對我釋出善意的台大中文系老師是吳宏一教授。
算一算,周老師當年借調暨大創中文系所時,也差不多是我現在的年歲。二○一五年的日子在倒數,這個月的日曆翻過去,我在埔里也就進入第二十個年頭了。二十年,正是我和先生之間年歲的差距。先生享年六十九,淋巴癌;逝於一九九七年的我的父親,也是淋巴癌,享年六十六。那也是我對自己年壽的推估的「天花板」。人生逆旅,總有到盡頭的時候。借鄭騫先生四十歲時之言,「能活滿易掛之數,已經甚為滿足」。昔日,愛讀周作人散文的周師,也愛引其「壽則多辱」的感慨(典出《莊子》)。而該做、想做的事,「要趕快做」。這是只活到五十六歲的魯迅的話了。
我真沒想到老師輩中最早走的是他。師長輩中,對我人生軌跡影響最大的並無第二人。聊述師生之誼,差堪告慰的是,這十多年來的學術和創作,並無愧於先生當年的賞識和期許。
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乙未冬,埔里